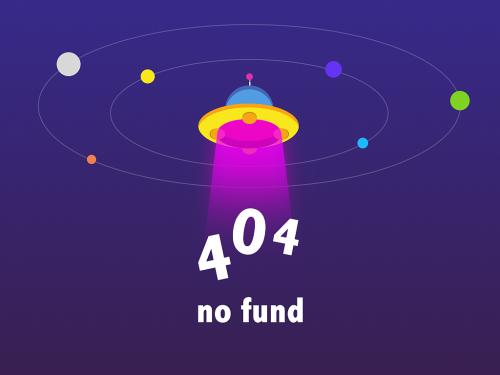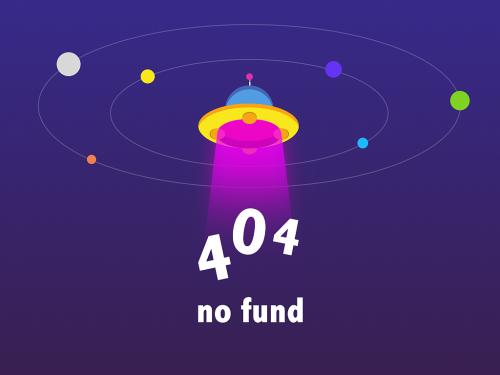以前从未想到能到一个建筑企业里工作。虽然建筑行业已经成了我们家乡父老从业人数最多的副业,但是,感觉它离我的生活总是很遥远。
还记得八十年代,村里同龄的那些结实能干的姑娘们辍学后都跟着本家的兄弟哥哥去城里打工。在建筑工地上从事搬砖、筛沙、推灰浆之类的工作。每当她们从城里回来,用挣到的钱给自己和家人买些衣裳用品,还说一些城里的见闻,对于当时还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来说是羡慕的。我央求她们带上我去,她们看看我单薄的身板,总是摇摇头,说你不行,干不了,吃不了那个苦的。
后来我也进了城,先是在一家报社做发行工作,后来又去机关单位做行业宣传。这其间,虽然与在城市里干建筑行业的同乡保持着联系,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走进他们的世界,体会他们的生活。建筑这个相对艰苦的行业,对我这样的体弱的女子,始终是拒绝的。
九十年代,有本家哥哥曾在我租住的效区附近干活,我去看望他,看见他们的住处在刚刚盖好还没有安上门窗的楼房里,四面透风。正赶上他们要开饭,用一个大锅炖的白菜,也给我盛了一碗,尝了一下,味道寡淡难以下咽;还有一位同学在一家建筑公司给经理开车,我们在莲池村住的时候,他们正在村前刚收获后的玉米地里盖后来的市政府三宿舍,那时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车也是破旧的;还记得同村的一位同样爱好文学的青年时常写信给我,说他曾在工作的工地上捡到一张登着我文章的报纸,郑重地带回老家珍藏起来。有一次他带着一身的泥浆和灰尘专程从很远的一处工地上来看我,却觉得我对他不怎么热情,很失落地离去。其实那只是缘自一份女孩的矜持而不是岐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向他解释,也无机会弥补。
值得欣慰的是,当年村里那些生活贫苦的人,现在都通过建筑这个行业,靠着自己付出的劳动和努力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每到农忙或过节的时候,在外干工程的人们开着一辆辆轿车回到村里,让人看着真是感慨良多:他们不再是传统观念里下苦力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的改变体现了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也体现了建筑业这些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如今,机缘巧合,我也来到建筑企业工作,近距离接触那些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脸被晒得黑黑的建筑工人们,心里感觉和见到家乡人一样十分亲切,仿佛一转身,就能听到他们在背后叫出我的小名儿。去公司施工的工地进行现场采访,看到施工区物料堆放整齐,洒水除尘设备齐全,生活区宿舍食堂厕所处处干净整洁,有空调,有浴室,还有净化水设备,办公和生活区绿化得也不错,有着花园似的感觉,让人一改以前对建筑工地的印象,内心不禁十分欢喜。心想回去一定要问问村里的那些乡亲们在哪里施工,工地的条件是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就赶紧动员他们到金城来吧。
潍坊分公司的一位同事曾对我说,有一天,他在工地上看到一位头戴安全帽的民工坐在那里看我们刚刚印刷发到工地上的报纸,都过了吃饭的时间很久了,他还坐在那里一直看,看得那么认真那么入神,让他这个旁观者非常感动,他把这份感动也传递给了我。想到我们采写编排的那些文字能给那些工地上辛勤工作的人们带去一份精神上的食粮,那么即使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吧。
在工作中,我更愿意去一线施工现场,把镜头对准那些用汗水盖起高楼大厦的人们,和他们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记录那些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和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